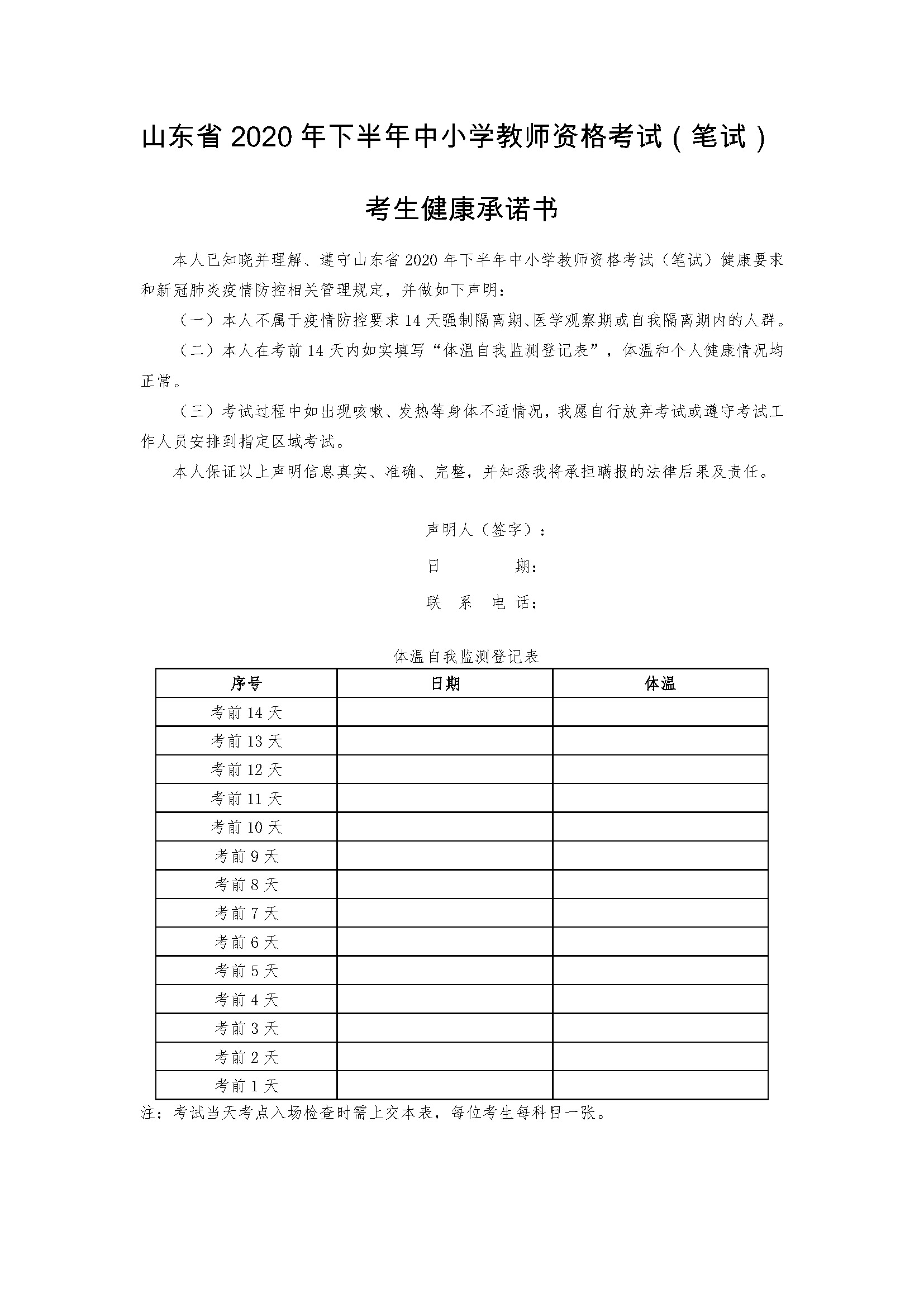安宁疗护社工:抚平生命最后时光的忧与愁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印发了《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提出安宁疗护实践以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以多学科协作模式进行;《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在人员配备中提出,除了医师、护士外,还可配备医务社会工作者及志愿服务等。
——由此可见,安宁疗护不只关乎医学,也关乎伦理、道德、社会等诸多领域。它不仅关心患者,也关心家属。
2023年,广州被列入第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地区,这对已在广州探索安宁疗护十多年的社工们也意味着更多机会。对终末期患者和家属而言,安宁疗护社工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安宁疗护社工的发展有哪些难点?广州的探索对更多的三四线城市是否有可借鉴之处?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就这些话题采访了多位社会工作者。她们表示,如果患者离世前没有经历太多痛苦,家属哀伤和愧疚的心情会少很多。

生命教育 谈论生死的“小组课堂”
清明前夕,广州市老人院的社工部部长、安宁疗护品牌负责人梁娟娟正在广州市老人院忙着筹备一场集体追思会,和老人们一起追忆离世的老伙伴。
她说,这是广州市老人院多年来的传统,每年都有五六十名老人报名参加,大家回忆故人,会谈及生死,有人也会谈起安宁疗护。
回想起2010年刚来到老人院开展安宁疗护社工工作时的不易,梁娟娟仍记忆犹新。
“老人们谈之色变,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吉利、很忌讳。”梁娟娟说,为了让老人更全面地认识安宁疗护,老人院决定将工作重点前移,将生命教育融入老人入院、在院的全过程,运用大家能接受的一切形式展开,追思会就是其中之一。
广州市老人院在住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其中95%以上是高龄体弱失能老人,每年约有150名老人离世。而他们的故事,不会因为离世而被遗忘。
追思会上,看着社工整理出的老友光影瞬间和故事,有的老人会羡慕离世时不太痛苦的老伙伴,也有的会想到自己还有哪些遗憾、还想实现哪些心愿。梁娟娟说,追忆逝者、探讨生死、重拾价值,这些都是追思会的意义。
是否选择安宁疗护,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如何看待生死紧密联系,老人们最感兴趣的健康讲座也成为带领老人打开生命教育之门的钥匙。梁娟娟介绍,生命教育通常以小组的形式展开,健康讲座上,带着老人们了解疾病、讨论生命,聊开了,老人们还会一起交流人生的乐事与遗憾,还有哪些话想对伴侣、子女、亲友说。平日里,社工还经常带着老人一起读书、做园艺,老友们凑到一起时会回忆过往的人生,有时也会探讨生命的意义。
在生命教育的后程,还会涉及生前预嘱、遗体捐献等领域,在院内的宣传栏里,也能看到相关内容。徐佩禹在广州市老人院从事安宁疗护社工已有3年多,起初,她很担心老人们会以为是“触霉头”,没想到老人们很感兴趣:“老人们是和新中国一同成长的,听到自己还能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他们都很高兴。”
随着生命教育的推进,老人和家属对安宁疗护的接受度一点点提高。2008年至今,广州市老人院累计服务安宁疗护的老人有1600多位。
徐佩禹记得,老人院里曾有一对年过九旬的教师夫妻,妻子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安宁疗护,只做对症治疗,如排痰、吸氧等。在丈夫眼中,妻子的终末期是不怎么痛苦的。结合妻子的个案,丈夫在社工的帮助下查阅了大量文献,将他对安宁疗护的思考写成论文。他在文中提及,安宁疗护并非宣扬一种消极的死亡观,而是贯彻治病救人理念的同时进行疼痛控制与心理舒缓的尊严死。后来,他也这样平静地离开了世界。
表达爱意 一封没有钱的特殊利是
在家属签署安宁疗护协议前,徐佩禹都会请家属和安宁疗护团队来到茶话室,开一场家庭会议,如果老人的身体情况允许,也会一同参加。
在广州市老人院,安宁疗护跨专业服务团队共有约140人,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营养师、康复师、护理员等,其中社工扮演统筹的角色。
与生命相关的会议,气氛是否会格外凝重?“大家围坐成一圈,房间就像家里的客厅一样敞亮。”徐佩禹说,面对危重症的患者,家属们往往会无助,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而这一会议能帮助家属理清思路——明晰老人的整体情况、明确安宁疗护能提供什么,以及他们还有哪些想做的事。
今年春节前,徐佩禹收到了一封特殊的利是,里边没有钱,而是一句“工作顺利”的祝福。在一场新春家庭聚会上,她所照护的九旬阿婆和家人、安宁疗护团队,一起喜迎甲辰龙年,圆了阿婆家人的一个心愿。
这一切,离不开安宁疗护团队的紧密配合。徐佩禹说,阿婆患有结肠癌和轻度认知症,医生在和家属沟通病情时,留意到家属提到了聚会。“很多时候,家属们并不确定老人院是否能做到、是否会麻烦工作人员、是否需要另外收费,我们主动对接家属,就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她说。
徐佩禹当天便联系了阿婆的家人,了解他们的构想。此后,还把备选场地、物料等都拍照发给家属,请他们远程参与挑选和布置。
当周的周六,徐佩禹和同事们为茶话室添上灯笼、气球、彩色蜡烛、鼓掌器,还买了一块蛋糕,一派新春的热闹景象。社工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回顾阿婆从年轻到如今的光影时刻,阿婆借着照片回忆起往事,还给女儿、女婿、孙子、亲家和工作人员们派发了祝福“利是”。“老人很喜欢派利是,一直在和我们说祝福,就像在家里过年一样。”她说。
聚会当天的照片,徐佩禹做成照片集送给了阿婆的家人,趁着阿婆状态尚好时留下了宝贵回忆。元宵节前,阿婆离世了。家属在料理完老人的后事后,还为老人院送来一面锦旗,表达对安宁疗护团队的感激。那封特殊的利是,徐佩禹一直留着。
哀伤辅导 用倾听和陪伴抚慰家属
患者离世并不意味着安宁疗护的结束,社工还会陪伴遗属走出哀伤。
徐佩禹记得,她曾服务过一位肿瘤晚期的阿叔,即使面色再差,他都会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他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好了随时都会离世的心理准备,唯独担心家人,尤其是妻子会承受不住。
徐佩禹说,那段时间,老人院为阿叔安排了双人间,请放心不下的阿姨一同参与照护。与此同时,每当老人院有手工、表演等活动,徐佩禹就邀请阿姨一同参加,转移阿姨的注意力。“可能我邀请的次数多了,阿姨也就不好意思不去了。”偶尔,阿姨趁着丈夫睡着、有医生照料时给自己“放假”,在老人院里逐渐认识了兴趣相近的新朋友。
两三个月间,阿叔的病情恶化,阿姨同意遵照阿叔的意愿不做抢救。徐佩禹记得,阿叔离世时,阿姨并没有哭,只是闷在房间里。徐佩禹静静地握着她的手,在一个多小时的沉默后,阿姨情绪的堤坝仿佛骤然“崩塌”,泪水夺眶而出。
哀伤需要时间来平复。最初的一个月,阿姨不愿意走出房间,经常翻着她和丈夫的聊天记录,徐佩禹就陪着阿姨,听她讲每一张照片里两人的回忆,协助阿姨料理一些后事,还为阿姨做了一本关于阿叔的相册。
后来,徐佩禹不时邀请阿姨一起去散步、逛花园,参加院内的一些活动。七八个月后,阿姨不再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便从老人院“请假”回家了。如今,遇到节假日,徐佩禹和阿姨还会在微信上聊几句,知道阿姨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能面对新的生活,她就很欣慰。
争分夺秒 找到最核心的需求
广州市老人院是医养结合机构,对入住多年的老人来说,老人院就是第二个家——老人、家属与社工、医护彼此都非常熟悉。而对于在医院开展安宁疗护的社工而言,一切都变得更为急迫。
田甜是益先社会工作研究院(以下简称“益先”)的执行院长,也是一名社工,她至今都难以忘记——有一位老人上午刚到医院,社工和医护人员完成了预估、家属面谈等,没想到午饭后就收到了患者离世的信息。
从2023年开始,益先在海珠区沙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田甜介绍,在多家医院辗转奔波、经历过多番化疗放疗之后,来到社区医院的患者和家属已能够接受“终末期”的事实,而患者的生存预期可能短至以月、日甚至按小时来计。“不同的生存预期下,患者和家属最紧迫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准服务?这是我们要探索的。”她说。
田甜告诉记者,由于终末期患者的身体情况很差,他们无法像常人一样进行完整表达,难以进行人生回顾等深度沟通。而经历了漫长的治疗期,家属也身心俱疲。社工能做的,就是协助患者与亲友进行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道愿、道谅,让患者尽量心无挂碍地离世。
这一经验,来自田甜的亲身经历。她曾陪着父亲抗癌3年。父亲在终末期时,“一天一个情况”,会突然呼吸窘迫、不能讲话,也会在打吊瓶时因烦躁而扯氧气面罩,“医生可能也很难给出有效的解决对策,看着他难受,家人也很无助。”她说。
如果是现在,她会建议家属,在用药的同时,可以给患者放音乐、讲讲安慰的话、做抚触,让患者感受到陪伴和安慰,舒缓患者紧张的肌肉,“有时这样安抚着,他(她)可能慢慢就睡着了,就像小朋友一样。”但当时,田甜没有答案,只能自己上网查、尝试和摸索。“所以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科普、整理一些经验,让家属们少一些无助。”
田甜举了个例子。当老人无法讲话时,不少家属都会待在病房里不知所措。而其实,呼唤老人的名字,握着他(她)的手,老人可能会发出声音,或试图睁眼——这些都是老人试图做出反应的积极信号。“我们会鼓励家属一边用热毛巾擦擦老人的身体、做抚触,一边和老人讲一些令他们放心的话,把老人当作宝宝一样。”田甜说。

密切沟通 与医护、家属“整合”缺一不可
田甜知道,还有很多家庭面临着与她相仿的困境。2017年,她就职于益先开始探索安宁疗护,并从2019年开始系统性地普查广州开展安宁疗护的机构,调研机构和从业者的困境和需求。在开展普查的同时,益先也和这些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搭建民间的绿色转介渠道,由医疗机构来评估患者是否符合收治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田甜也在探索“医、护、社”整合式安宁疗护。田甜解释,传统的医疗着重于救死扶伤,要用尽方法解决患者的症状,而安宁疗护比起生命的长度更关注生命的质量,“这一决策涉及大量的沟通,需要确保大家有统一的照护目标。”
在田甜看来,和医护的紧密合作是在社区医院进行整合式安宁疗护的基础,“任何一个专业缺位,都意味着患者整体性疼痛的某一方面被忽视了。”在沙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的个案开案前,医护和社工会一起制订评估计划;每周入院探访老人前,社工会和医护再了解老人的最新情况,社工发现的情况也会及时和医护同步;每个月,安宁疗护团队的医护和社工都会定期开会,整体性分析患者近期的状况,以便制订下一步的照护计划。“在社区医院,我们不只是协助医生链接患者所需的社会支持,也深度参与到安宁疗护过程之中。”田甜说。
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体对死亡和疾病的看法都不相同,面对家属和患者,社工更多是结合经验,帮助他们在迷茫中找到可能的选项。
田甜记得,她服务过的家属刘先生(化姓)曾有一段时间因“为父亲插管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而焦虑。刘先生说,插管后的父亲不能说话,看起来没有生活质量;可如果当初不插管,父亲就真的走了。田甜和同事引导他思考父亲日常的表达、对疾病的态度。“想到父亲一定会选择和疾病战斗到底,他也就释怀了。”她说。由于父亲病情恶化,刘先生又向社工求助寻找安宁疗护的机构。田甜和同事们多方对接,最终帮助刘先生找到一家合适的机构,他的父亲后来在那里离世。
还有的家属出于善意对患者隐瞒真实病情,从而令患者对治疗还抱有一定的期待。在不确定性的纠结中,“拖着”成了一个最常见的选择,直到患者真的意识到大限将至,可能也错过了很多深度沟通的机会。田甜说,面对这些具体情境,任何抉择都没有对错之分,社工能做的,就是基于之前的大量案例,告诉家属可以有哪些选择、各有哪些利弊,由家属来作决定。

未来发展 用广州经验带动更多行动者
有研究指出,基于综合医院门诊、住院、社区及养老机构等服务场景,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医疗机构配有专职医务社工,医务社工参与安宁疗护服务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由于医务社工主要服务重病患者,对社工能力的要求很高。在广州市老人院,每个月会定期举办安宁疗护相关的培训。梁娟娟表示,由于我国尚未将安宁疗护和生命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体系,导致专业的安宁疗护人才极度缺乏。因此,她建议针对安宁疗护服务团队要展开更有针对性的培训,增强从业者对相关概念的认知。同时,还要加强对团队成员的心理干预和辅导,特别是长期接触终末期病人的医护人员、社工和志愿者。
“不赚钱、没方法,这是很多人观望安宁疗护的原因。”田甜介绍,今年,受第十一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支持,益先将面向愿意在社区开展安宁疗护的机构开展赋能计划,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将此前积累的具体化、情境化的案例与大家一起讨论。参与的机构不只是“听讲”,也要分享机构自身的实践,大家共同研讨后将形成案例集。目前,珠三角地区已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机构表达了参与意愿。
有研究指出,目前安宁疗护服务中社工服务收费标准缺乏。国外的安宁疗护机构多为福利性质,大多能得到慈善捐款,而我国的安宁疗护机构目前还不属于慈善范围。在广州市老人院,疼痛评估、心理疏导、哀伤辅导等服务均为无偿服务。对益先而言,资金主要来自购买服务的医院、自筹以及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等项目的资助。
2023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推动将机构和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费用逐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其他补充医疗保险范畴。在资金支持下,安宁疗护的可持续发展和质量提升或将迎来新的可能。
2019年,依托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资助,广州市老人院和益先联合多家养老服务与研究单位举办了广州市安宁疗护服务交流会,吸引了外省的从业者参加。作为一线城市,广州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较为丰富,社工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对更普遍的中小城市而言,广州的探索有什么借鉴意义?
田甜告诉记者,益先正在建立跨区域的安宁疗护联动网络,目前已有6省(市)的68家单位参与,其中有的医院和养老机构未必有完整的多专业协作团队,靠着热情来探索。“从转变理念开始,我们鼓励更多人行动起来,因地制宜开展安宁疗护。”她说。
田甜举例,比如在日常的照护中多一些问候、用棉签护理伤口的手法从摩擦变为滚动等,“哪怕只能做到这些细节,也是在带着安宁疗护的理念照护。”今年,益先还将结合已有的经验拟定安宁疗护指引,让有心但资源有限的机构也能加入到安宁疗护的行列中来。
版权声明:本文为三牛号作者或机构在本站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本站的观点或立场,三牛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